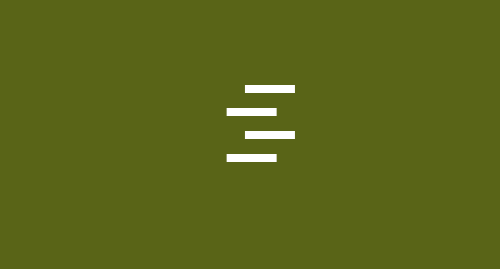约翰·萨尔瓦多大公是梅耶林的第三名受害者
梅耶林的悲剧无疑敲响了奥匈帝国的丧钟,就像当初“项链事件”(1)是法国革命的先声一样。
有一个人,他的一生因梅耶林的两人死亡事件而完全变了样。如果说,那次悲剧还造成了第三名受害者,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此人名叫约翰·萨尔瓦多,是托斯卡纳的亲王,奥地利大公。他是大公利奥波德二世(2)和西西里的玛格丽特公主的儿子。在巧合所造就的各种命运中,很少有比他的命运更奇特、更怪诞、更扑朔迷离的了。他在奥地利的宫廷里长大,是只新的雏鹰。当他的父亲被迫从托斯卡纳王位上隐退以后,他很快就表现出超人的智商,人们毫无讽刺意思地说,他的聪明在哈普斯堡家族是一例外。
曾担任过法国大使,认识所有欧洲执政王族的莫里斯·帕雷奥洛格对他是这样描写的:“个子高大而灵活,身材瘦削,面部轮廓坚毅,嗓音热情而颤抖,很少做手势。总之,在所有方面都显得潇洒而高雅。”此外,“他酷爱文学、艺术和音乐,愿意与人交谈,同朋友来往;喜欢打猎。当然,他也同样乐意追逐女性。”虽然他的风流韵事很多,有时几件艳遇同时发生,但是,每次“都显得那么美好动人,那么神秘而又富有诗意”。
他对艺术也是内行,他把他在萨尔茨康迈尔古特的奥尔特城堡变成了一座私人博物馆。在那里,人们每走一步,就可以欣赏到稀世宝物,如古画、塑像、雕刻、青铜器皿、奖章、陶瓷、珠宝、银器、铁饰品、兵器、盔甲、绸缎、家具等。
这位与众不同的大公又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曾经成功地在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芭蕾舞剧“杀人犯”。
他24岁时已经是上校,29岁就当上了将军。显然,他能如此平步青云,他的出身带来的“权利”比他个人的能力更重要……而这恰恰是约翰·萨尔瓦多的内心隐痛所在,因为他感到自己有力量和毅力去得到最高一级的职务,因此一想到他的级别是因他的大公头衔才获得,他就火冒三丈。
他最讨厌特权与优待。当他看到在军队里,在他周围的人中,错误地将某些领导官职位交给一些不称职的人时,他更是怒不可遏。他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决定抛出一颗炸弹。
当第二兵团司令、托斯卡纳大公约翰·萨尔瓦多将军的小册子《烦恼还是教育》公开出售时,这也在维也纳成了前所未有的丑闻!一名王族的亲王居然敢批评军队的组织机构,称高级指挥部“傲慢无礼”;他竟敢透露说,公布的有关数字是假的,指责防御工事已经陈旧过时,批评后勤部门无人过问;最后他还攻击了“敬爱的首长们”。
在霍夫堡,弗朗茨瓦·约瑟夫老皇帝因激动和气愤差点昏了过去!对约翰·萨尔瓦多来说,后果马上见分晓:他的小册子被人竞相抢购,但他本人则被放逐到林茨。
他的情妇、漂亮的卢德·米拉·施图贝尔是歌剧院的可爱的舞蹈演员,她也随同前往。他是在1885年秋天认识她的。当时她才16岁,是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评论家们早已称赞她很有天赋。约翰·萨尔瓦多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她有倾城之貌。这一判断也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人很欣赏她的瓜子脸蛋,大而深邃的眼睛,又长又黑的秀发,白皙的皮肤,瘦长的身材,长而有力的小腿。她的一位熟人居然说她“像希腊雕塑一样美丽”。

图三十六 大公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
他们的邂逅是一则优美的故事。“米莉”不正是因为他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才委身于他的吗?这证明她的爱情是多么纯洁真诚。
在林茨,心爱的米莉的陪伴也无法消除约翰·萨尔瓦多心中的积恨:弗朗索瓦·约瑟夫不但不考虑他的批评意见,而且还借此机会排挤他、污辱他。约翰·萨尔瓦多开始策划,他毫不隐瞒他的目标:迫使老朽的弗朗索瓦·约瑟夫下台,逼他让位于他的儿子鲁道尔夫。
约翰·萨尔瓦多将此计划告知鲁道尔夫。后者毫无拒绝之意。两位堂兄弟碰头,策划,提出宏伟目标。他们交换意见时,言词与思想同样激烈。他们毫无戒心地通过邮局互寄宪法草案和公开表达革命思想的信件。这太不谨慎了,信件全部被查收,阴谋全部败露。
鲁道尔夫倒霉了。约翰·萨尔瓦多也倒霉了。前者是王位继承人,从此被排斥在任何权力之外,被人看守监视起来。对于约翰·萨尔瓦多来说,顷刻间他的一切全成了泡影,军衔、荣誉、爵位,这一切全因“损害帝国安全”而被取消。
约翰·萨尔瓦多感到失望、沮丧,带着米莉躲进奥尔特城堡,他开始出门远游。有一天,传来可怕的消息,鲁道尔夫在梅耶林自杀身亡。约翰·萨尔瓦多心里不是不知道,对于他的死,自己也有责任。不正是他的阴谋计划泄露出去后,才使得鲁道尔夫无法活下去的吗?
托斯卡纳的约翰对此的反应,早已为我们所知。他不断地重复:“我不应该,也不能够也无法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了……我再不愿当大公了,我再不愿当殿下了。也就是说,再不愿当一名自命不凡的傀儡,一名过时的模特儿。我愿作一个人,我愿只凭良心行事,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思考,随心所欲地行动……我的新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放弃我的特权,不再过那种我的大公同僚们津津乐道的游手好闲、豪华浮夸、纸醉金迷的生活。我将只靠我个人的微薄财产的收入过活,不再领取帝国金库的一个弗洛林或一个克烈采(3)……”
他很快得出以下符合逻辑的结论:“我将按照最有礼貌的方式向皇帝表示,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体制不适用于我,我不再属于皇族。以此推论,我放弃我的地位、称号、特权和所有大公享有的特殊待遇,我今后只是一名普通人,用的是普通市民的名字约翰·奥尔特……”
他的母亲和兄弟最先知道约翰·萨尔瓦多的最新决定,他们恳求他打消这一念头,不要让哈布斯堡-托斯卡纳家族蒙受这一奇耻大辱,但毫无结果。约翰·萨尔瓦多将请求送给弗朗索瓦·约瑟夫。显而易见,皇帝欣然同意。他很快就回信接受请求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不仅仅是同意约翰·萨尔瓦多的请求,更有甚者,他用取消大公的奥地利公民资格作为回敬。这说明积怨多么深。这样一来,约翰·萨尔瓦多就无权在皇帝管辖的各州居住了。这个不可逆转的决定于1889年10月16日正式颁布。
这意外的最后一击打得约翰·萨尔多瓦晕头转向,打击太大了。这样一来,约翰·萨尔瓦多在自己的祖国倒成了外国人了!
但是,当他从最初自然产生的沮丧情绪中摆脱出来以后,这位前大公的决心更坚定了。
公元1890年3月26日,船长索迪赫驾驶的双桅帆船“圣玛格丽特号”离开了朴次茅斯港。
“圣玛格丽特号”上载了一名乘客,这名乘客同时又是船东,他是奥地利人,名叫约翰·奥尔特。约翰·萨尔瓦多严格遵照自己拟定的计划,改换了姓名,这样他同时就取得了新的人格。什么亲王、大公,统统结束了。现在,他是航海家约翰·奥尔特,他前面的航道已通行无阻了。
那么卢德·米拉·施图贝尔呢?约翰·奥尔特1890年从奥地利出发时,首先把她带到苏黎世,然后又带到伦敦。毫无疑问,米莉也陪同情夫上了“圣玛格丽特号”船。在维也纳,在霍夫堡或在上层人士中间,人们谈论他们,或者不如说是私下议论他们。
那艘双桅帆船渡过了大西洋,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1890年7月10日,约翰·奥尔特给他在维也纳的朋友、记者保罗·海因里希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他第一次航行表示满意。他计划再次出发去探索火地岛和好望角地区。他还补充说,他很惋惜地将船长索迪赫留在岸上,因为他病倒了。“我就自己驾驶‘圣玛格丽特号’。”同一天,他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之后,就是谜了……
因为,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见到“圣玛格丽特号”。约翰·奥尔特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风浪之角(好望角)一带,人们从未发现可以使人猜出船舶出事的任何船舶的残骸。
官方讣告反复宣布“托斯卡纳—霍夫堡的约翰·萨尔瓦多大公已于1890年7月,在霍恩角触礁身亡。”弗朗索瓦·约瑟夫皇帝本人也正式承认了这一死讯。
真是这样吗?
但是,约翰·奥尔特的母亲、托斯卡纳的老大公夫人玛格丽特并没有身着丧服。
奥地利当局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好望角四周寻找触礁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另外,令人奇怪的是,“圣玛格丽特号”上的水手家属也没有提出任何申诉。
只有某些迹象表明,“圣玛格丽特号”曾于1890年12月在拉普拉塔停泊。约翰·奥尔特给海因里希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从那里发出的。从7月到12月,约翰·奥尔特大概在阿根廷呆过,不过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对此问题写过一部优秀著作的乔治·德拉马尔指出:“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研究其他假设时,我们将会发现,阿根廷的警察局对于外国人一直是非常警惕的”。
上述不正常现象自然引起了一场争论。
当人们突然得知,一位维也纳旅行家声称他在西班牙见过大公后,争论就更加激烈了。这位旅行家被人穷追不舍地问及此事时,很痛快地具体说明,他在“离托莱多不远的一座修道院里,清清楚楚地看见大公穿着道士长袍”。此事发生在圣周(4)。这位维也纳人被获准参加耶稣苦难纪念三日大课。他呆在小教堂一座门附近,当仪式接近尾声时,他虔诚地观看修士们列队走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在修士中,认出了托斯卡纳亲王,当时,他的风帽只盖住一半头部。是他,绝对没有错!他在维也纳见他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是不会弄错的。不过,大公一闪而过。第二天,旅行家急忙赶到寺院长老那里,求他讲出实情,因为有那么多的奥地利人渴望了解真实情况。长老摇了摇头,说:
“迈过我们门槛的基督教徒已脱离红尘,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
绝妙的故事!不过,旅行家似乎有点想入非非。在宗教方面,大公不信神是众所周知的,有些人甚至说他是无神论者。他突然皈依,并且立即大彻大悟,太离奇了,所以不能成立。
再说,就在同一时期,一位南极探险家断言,他在格雷厄姆地附近的若因维利岛上同一个人谈过话,此人的公文皮包“丢在房间的桌上”,皮包上有奥地利王室的凸起盾形纹章。毫无疑问,此人就是大公。
另一位奥地利商人的叙述显得更可取一些。他曾于1899年经过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三国之间的大查科草原。他同一名叫菲德烈·奥滕的德国人取得了联系。德国人在阿根廷与智利之间有争议的地区的沙漠中买了一座庄园,它离最近的人家也有20公里。这位商人也认为自己认出了约翰·奥尔特。这使人感到困惑,但是不说明问题。
只是到了后来一年,人们才搜集到一些准确的消息。1900年11月,一名乌拉圭议员欧金尼奥·加尔佐内参议员对约翰·萨尔瓦多大公失踪的传说发生了兴趣,决心解开这个谜。他的调查结果已载入他的著作《约翰·奥尔特》中,此书已有法文译本在法国出版。
他先去了拉普拉塔。他查阅了商船的登记册,询问了一些目击者。他很快就坚信,“圣玛格丽特号”曾停泊在那里,只是到了1890年12月才离开。
这之后,他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得到内阁批准,查阅了警察局档案。一开始,毫无线索,没有任何关于同前大公的外表相似或大致相似的外国人的消息。首都警察局绝对没有给一名叫约翰·奥尔特的奥地利人发过居留证。
但是,欧金尼奥·加尔佐内并不因此罢休。他成功地使一位高级官员对“他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位官员被牵连进来之后,向“中、小城市的警察分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官员提供外表与约翰·萨尔瓦多相似的人的所有情况。结果令人失望,人们说见过许多外国人,甚至见过一些奥地利人,即使拥有人类最强烈的意愿,他们中的任何人均不能被认为是大公,因为总有某一个细节不符。欧金尼奥·加尔佐内也好,那位高级官员也好,他们均不气馁,他们的劲头反而更大。乌拉圭恩特雷里奥斯省边境城市孔科尔迪亚的警察局长总算送来一份使人震惊的报告:
“在去年(1899年)年底,我手下的人注意到一名住在普通旅馆的外国人。我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找到旅馆老板,向他询问了情况。老板说,他的房客单身独居,西班牙语说得不好,有日耳曼语口音。他神情忧郁,不去那些游乐场所,也不与任何人来往。”
“在谈话中,旅馆老板向这名工作人员说,一名负责打扫这位外国人房间的女工,趁他不在房间时,在桌子上拾到一枚挂在授带上的十字形勋章。”
“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并且弄清楚他尚未按照有关国土安全的法令,在我手下的机关登记姓名职业之后,就向他发了一张传票,因为我想亲自见他,”
“他痛快地应召前来,我接待了他。他的高雅的风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见到的是一位50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稀疏,胡须均已花白,眼珠呈蓝色,举止像军人。他讲西班牙语时口音很重。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外国人自称是约翰·奥尔特,是奥地利人……”
真是戏剧性的变化!欧金尼奥·加尔佐内已经一劳永逸地使真相大白了吗?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警察局长进一步说明,约翰·奥尔特曾在孔科尔迪亚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与一位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农场主接上了关系,并且在那里定居,饲养马匹。
参议员急于得到其他细节。约翰·奥尔特此刻在何处?他在干什么?警察局长的最后一封信简单明了地使欧金尼奥·加尔佐内的幻想破灭了。他写道:“此人已去日本。”
乌拉圭参议员这下子只得死心了,这也可以理解。他不能因为对历史秘密的癖好,也去日本一趟。
事情到了亚洲。奇怪的是,在拉里什伯爵夫人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了这一大陆。当然,玩弄阴谋诡计的女人的回忆录总是靠不住的。人们经常轻易地发现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下错误。但是,在伯爵夫人的叙述中,并不全是虚假的。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她的叙述。
拉里什伯爵夫人写道:“奥地利宫廷知道得清清楚楚,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经湮没无闻的前大公,而且实际上一直掌握这一情报。然而,K公主的姐姐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了解到约翰·奥尔特的藏身之处,因为人们对此守口如瓶。再说,前大公本人也极为巧妙地故意搞乱了线索。”
“汉斯·维尔切克伯爵同时为托斯卡纳的约翰和克龙普株茨·鲁道尔夫两人的好友。他过去曾经常在奥匈帝国舰队的船籍港波拉见到前大公。维尔切克是极地探险家,对航海问题兴趣浓厚,对于海洋方面知识广博。他认为,声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触礁,只不过是像托斯卡纳的约翰这样有经验的军事战略家的一种金蝉脱壳之计。前大公考虑十分周密,他甚至于带上不同报纸与船上证件,好让任何人也不会怀疑他的船是‘玛格丽特号’。他首先在奥地利雇佣了一批船员,但是,在第一次停泊时,他又将所有船员解雇了。之后,大公又略施小计,将他的船改头换面。他做得非常成功,谁也没有认出它来。维尔切克从一位海军军官那里得到了其他细节。他过去在前大公手下的人中间,曾见过这位军官。”
“‘玛格丽特号’改名之后,航遍了世界各大洋,遇到过多次风暴。在一次大风暴中,约翰·奥尔特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一位船员。船员名叫本奇尔,是一位瘦瘦的棕色皮肤的东方人,他整天愁眉苦脸,但又举止高傲。约翰·奥尔特曾多次发现,这位年轻的海军下士与其他的老水手完全不一样。”
“本奇尔被救之后,他的茫然的目光投向约翰·奥尔特,向他鞠躬并且说:
‘……你救了我的命,船长。请允许我随时留心保护你,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救你一命!’”
“他说完之后就转过身去,继续干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几个星期之后,约翰·奥尔特还是出于扰乱线索的考虑,又换了船员,航行时用第三本航海日记,在所有的船员中间,他只留下了本奇尔。他还为他的游艇取了个新名:‘伊纳塔号’,即陌生者的意想。他沿长江而上,最后在唐古拉山脚下定居。在那里,他在米莉·施图贝尔和他的私人侍从本奇尔的陪伴下,过着平静的日子。”
多么动人的“奥德赛”!
我们应该简单地说明,关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触礁的说法纯系臆造;船名也不是“玛格丽特号”,而是“圣玛格丽特号”;船员也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朴茨茅斯雇佣的。
但是,拉里什伯爵夫人并未到此却步。传闻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在上海郊区见到了大公。一名“为K公主的姐姐效劳的”侦探得知了工程师的秘密。他马上出发去寻找大公。但是,他却“突然死去”。而那位奥地利工程师也“自杀了”,因为“他为自己背叛了过去的领袖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之后,K公主本人也急忙赶到远东,来到中国,来到唐古拉山。她在那里听说,一名叫乔瓦尼·奥尔特罗的意大利人和他的年轻妻子曾在该地定居。她赶到他家里,结果“正好面对面地碰上大公”。
“殿下,感谢上帝,总算把你找到了!”
男人摇了摇头,说:
“实在抱歉,夫人”,他用意大利语说,说完之后还作了一个漂亮的敬礼姿势,“很遗憾,你说的语言我听不懂”。
K公主只得退了出去,心中万分沮丧。
拉里什伯爵夫人是“通过另外的途径”才了解到大公故事的下文的。乔瓦尼·奥尔特罗见到公主后的第二天,对他的妻子和本奇尔说:
“我们的宁静被人偷走了。我们应尽快离开此地。本奇尔,现在我全靠你了。把船准备好,雇佣好船员,我们好继续出发远游。”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本奇尔这才透露,他原是亲王,出生在波斯,是穆扎维尔·埃德·德辛国王的侄子,因为政治原因被放逐。他刚刚得到特赦,因此,他“邀请约翰·奥尔特去他的祖国作客”。
拉里什伯爵夫人最后说:
“约翰·奥尔特就这样上溯波斯湾,在喀什米尔国的著名的玫瑰谷定居下来。当维尔切克伯爵给我讲述这段故事时,他仍住在那里。我曾答应伯爵说,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能将他对我透露的消息散布出去。但是,他于1920年去世。这样我就不再受誓言的约束了。
正如乔治·德拉马尔所指出的那样,喀什米尔并不在波斯,而是在印度……这一切讲完之后,只有请读者自己去判断这位维也纳伯爵夫人的说法是否可靠……
莫里斯·帕雷奥洛格的小册子出版以前,争论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本小册子于1959年发表,题目是《大公约翰·奥尔特的奇特命运》。
约翰·萨尔瓦多失踪后整整70年,谜底好像最终被揭开了!为此,我们应感谢莫里斯·帕雷奥洛格和感谢出版商为我们出版了这部遗著。
莫里斯·帕雷奥洛格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不仅搜集了“据说”和那些自相矛盾的传闻,而且掌握了一份无可辩驳的证词,即法国人让·德利尼埃的证词。
让·德利尼埃自1900年以来一直定居阿根廷。他是旅行家,又是探险家,他曾长时间地访问过安第斯山最难攀登的地区。经过几年探险生活之后,他在该国南部别德马湖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当时,那里还十分荒凉,最近的城市圣克鲁斯小港,离那里还有450公里!
公元1907年10月的某一天,他骑马经过菲茨罗伊火山口下面的地段。此时,他看见在沙漠中有一大窝棚,一个敞棚和一座帐篷,周围还有一些马,几只牛。
一名男人出现在窝棚的门槛上,“他大约50岁,个子高而身材瘦,胸脯挺直,头发灰白,胡子剪短,五官清秀”。他身穿皮衣,脚穿高统皮靴。
这位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西班牙语向他问候。又出来两个男人。第一个男人向让·德利尼埃介绍另外两人:
“这是我的两位伙伴……两位朋友……尼科尔森是英国人,赞德·杰克是德国人。”
两个牧场之间建立了频繁的关系,两者之间相距约80公里。第三次见面时,那人终于下决心德向利尼埃作自我介绍:
“我叫费雷德·奥滕……奥地利人。”
费雷德·奥滕!人们还记得起,这正是一名奥地利商人1889年通过大查科草原时所见到的那位“德国人”。他当时认为,这位德国人就是约翰·奥尔特。
也许,德利尼埃并不知道他的假定的身份。但是,“通过赞德·杰克和尼科尔森或明或暗的影射,通过他们对牧场主的毕恭毕敬的态度,通过他在密切的共同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种种细节”,德利尼埃终于明白,他遇见的是托斯卡纳·哈布斯堡家族的约翰·萨尔瓦多。
终于有一天,费雷德·奥滕自己也承认他就是约翰·奥尔特!
他失踪后的遭遇如何?他通过断断续续的谈话,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首先,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漂亮的卢德·米拉并没有陪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在伦敦就分手了。一部罗曼史宣布结束。
“圣玛格丽特号”于1890年7月10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之后,一直驶向巴塔哥尼亚。约翰·奥尔特在那里居住过,而且住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又在麦哲伦海峡两岸所有荒凉的地区进行探险。这种生活虽然艰苦,但却振奋人心。他这样生活了许多年头。这位隐世的大公最后在菲茨罗伊火山脚下定居下来。1907年,德利尼埃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
这就是这位法国人的说法。这一说法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它似乎也有一些缺陷。既然那位奥地利商人于1899年在大查科草原与大公邂逅,他又怎么从麦哲伦海峡直接去了菲茨罗伊?看来,约翰·奥尔特可能在阿根廷北部某地待过一段时间。
还有,人们在孔科尔迪亚所遇见的也是同一个外国人吗?为什么大家说他去了日本?
公元1909年12月中旬,德利尼埃回到法国去谈一桩生意。1910年年底,他又回到圣克鲁斯。他听说,“费雷德·奥滕”已经在前一年的冬天去世。
这位神秘的大公永远安息在安第斯山的脚下了。
【注释】
(1)项链事件,1785年在法国发生的丑闻。拉莫特伯爵夫人与失宠的红衣主教罗昂串通,用伪造王后安托瓦内特签字的办法,将一枚价值160万镑的项链买回送给王后。事情败露后,全国大哗。舆论界谴责王后奢侈。后来法院只好判拉莫特夫人与红衣主教无罪。这一事件使王朝威信扫地。
(2)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时国王。
(3)弗洛林、克烈采均为当时奥匈帝国的货币。
(4)圣周,指复活节前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