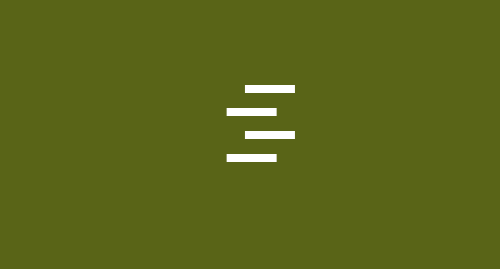一天深夜……
“我常常在想,”米克·巴卢说,“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会有什么不一样。”
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地狱厨房”的葛洛根开放屋,他经营这家酒吧已经很多年了。尽管酒吧的风格从里到外都没怎么变,但还是能看出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化对葛洛根带来的影响。以前那些难缠的客人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现在的客人要优雅、绅士得多。柜台上供应散装的健力士,也摆了不少单一纯麦苏格兰威士忌和其他上好的威士忌。但吸引客人的,仍然是这酒吧彪悍的名声。大家指着墙上的弹痕,聊起店主臭名昭著的往事。有些故事还真的发生过。
现在客人们都走了。酒保打了烊,把所有椅子都倒扣到桌上,省得早晨杂役来打扫拖地的时候碍事。门上了锁,灯都关了,只有我们俩的桌子上方还留着一盏灯。我们面前放着两只沃特福德酒杯,米克的杯里装着威士忌,我的则是苏打水。
这几年,我和他在酒吧夜聊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年纪大了,我们既不乐意跑去佛罗里达,在附近的家庭餐馆吃什么“晨间套餐”,也不乐意彻夜长谈,最后睁大眼睛迎接黎明。我们都过了做这种事的年纪了。
他现在喝得比以前少。一年多以前,他结了婚,那女人比她小得多,名叫克里斯廷·霍兰德。这桩婚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只有我太太伊莱恩没觉得意外,她发誓早就看出来了——他也的确因此有所改变,只是因为有个牵挂让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仍然喝十二年藏的尊美醇威士忌,不加冰块不加水,但喝得没有以前多,有些日子干脆滴酒不沾。“我仍对酒持有兴致,”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渴得过分,但现在这种渴意已离我远去。我也不知道它去了哪儿。”
早些年,我们倒是经常在酒吧熬通宵,边喝边谈,偶尔也会沉默不语,各自喝着他指定的酒。黎明时分,他会系上父亲传下来的血迹斑斑的围裙,去肉类加工区的圣伯纳德教堂参与屠夫弥撒。有时我会陪他一起去。
时过境迁。肉类加工区如今是雅皮士聚居的潮流之地。大多数肉类加工厂也都停业了,原来的厂房变成了餐馆和公寓。圣伯纳德原本是爱尔兰教区,现在也成了瓜达卢佩圣母的领地。
我不记得上次看见米克系那条围裙是什么时候了。
今天这种夜聊好像挺少见的,而且我们都觉得有必要留下来谈一谈,不然现在早该回家了。米克看起来若有所思。
“另一条路,”我说,“什么意思?”
“有些时候,”他说,“我觉得好像别无选择。我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路的。可最近我不那么看了,因为现在我的生意干净得像犬牙一样。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说像犬牙?”
“不清楚。”
“我得问问克里斯廷,”他说,“她坐在电脑前,花三十秒钟就能捣鼓出答案。当然,前提是我记得问她。”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微微一笑。“可当时我没能认清,”他说,“我变成了一个职业罪犯。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不是什么先例。我住的那块区域,最主要的职业就是罪犯。周围的街道真是职业罪犯的培训所。”
“您可是优秀毕业生。”
-
-
下载参考地址:
-
一滴烈酒.epub
-
-
-
- 温馨提示:
- 在微信、微博等APP中下载时,会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
- 这时请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然后再请下载浏览
-